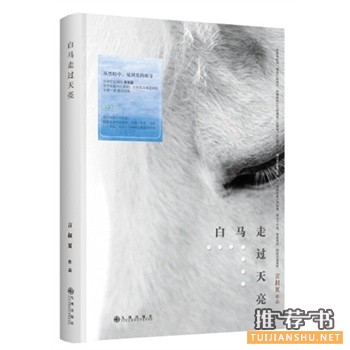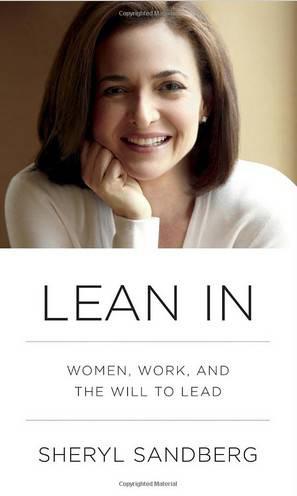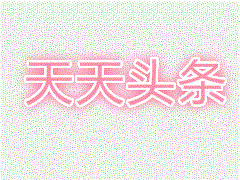《白马走过天亮》最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书! 推荐书为您搜集购买地址,请放心购买:
【淘宝购买地址】
【京东购买地址】
【亚马逊购买地址】
【当当购买地址】
[出版信息] 书名:《白马走过天亮》 作者:言叔夏 出版时间:2014年9月 定价:30.00元 出版社:九州出版社 ISBN:978-7-5108-3125-6 [书讯] 十年里我做了什么?去了一个不喜欢的城市,搬四次家,和三个人分手,换了六份工作。十年里外婆死了。从**南部小镇到东部乡间,再到城市盆地的人事流转;上课、房间、衣蛾、家人的死亡与好友的别离这是一个孤独的年轻女人,和她人生中最重要的十年。好繁华的街一整条灯如流水,好勇敢的灯已经撑起一匹黑夜,好辽阔的夜又淹过来整条的街,每一间餐馆都人声鼎沸。我往下行走,譬若夜游,宛如沿途卖梦。带着羚羊般跳跃的意象,言叔夏以极为世故又极为澄澈的文字,和被时间淘洗却益发光亮的天真,欲语还休地道出生命中的伤害、失落、启悟,与难以言喻的感思。泯灭爱与残酷、梦想与死亡、温暖与冰冷的界限;在倾斜琐碎的世界中,以字织茧,呵护一个既晦暗又纯真的世界。 [作者] 言叔夏,1982年生。东华大学中文系、政治大学中文所毕业。现为政治大学**文学研究所博士生。曾获花莲文学奖、台北文学奖、全国学生文学奖、林荣三文学奖。 [名人推荐] 这不再是一本散文集了,而是一本诗集,一部超现实的画册,或者杨·史云梅耶的动画,甚至一页页的纸上电影。——**作家 郝誉翔 她在荒谬和生活之间找到书写的位置。日常的琐碎,童年和青春,都带有预言和梦的特质。情感细腻,带着诗意的想象,以及“一切怎么如此荒谬”的无奈和欲言又止。——马华文学作家 钟怡雯 [书评:在梦境里我们是自由的] 《白马走过天亮》:在梦境里我们是自由的 文_满成蛟 在忙碌的工作间隙,花了好些时间才终于看完言叔夏的新书《白马走过天亮》。同名的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《自由时报》上,后来陆续在多本集结书里出现。看完整本书,会感觉言叔夏是活在梦里的人。在梦里可以是诗化的,死亡的,哲学的,自我的。欧阳江河说,这个世界上,读诗的人比不读诗的人幸福,但现实是诗歌没落了,可你在《白马走过天亮》里,处处可以看到诗歌的影子,这里不仅有诗歌的意象,更有诗歌化的表达。 “那个冬天地窖里冥王星般的房间,像巢穴,又像是一个黑洞,灌注满有毒的奶水。克里斯蒂娃说母亲我是你的呕吐物。你生下了我就吐出了我。是遗弃的动作?被呕吐的感觉?还是恨的其实是那只生我的子宫?” “时光队伍在白天鸟兽般地散开,在梦里成群结队地回来,在睡眠里围着营火齐声歌唱,然后在苏醒里被全部遣返。” 这些句子全部是言叔夏对生活诗意的理解,但这种诗意里面更多是带着一种悲伤的氛围。这种悲伤让她不住地在文章中书写死亡,书写梦境,书写对母亲的厌恶,书写在地下室孤独生活的模样,以及童话式的臆想。 《袋虫》一文里,言叔夏洋洋洒洒几千言书写自己的房间和一只闯入的蛾子,那只是房间么?显然不是,那是她孤独敏感的内心。《鱼怪之町》,借着一个通话故事的影子,她更是书写了一个童年时的噩梦。那个被塑造的变成海鱼拥抱海水的故事,让她一度怀疑生活不如意的母亲曾试图带着她在海边跳海自杀。 言叔夏是悲伤的?言叔夏是悲伤的! 但是我们究竟有多久没有悲伤过了?某日在地铁上,看《白马走过天亮》时,脑子中突然出现一句话,没有纸笔我便掏出iPad平板:“我们是有多久没有面对自己的内心了?”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打鸡血的成功学读物,随处可见垃废话被包装成的心灵鸡汤。我们拼命赶路的时候,已然忘记了我们不是生活的机器,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有喜怒哀乐,有悲欢离合的“人”。 所谓的“大数据时代”,磨灭了我们“人”的属性。《白马走过天亮》是一杯忧伤的读物,书写生活的时候,也极力地反抗着心灵鸡汤式的生活。作者在试图唤醒我们,去重新发现我们的内心。 一篇篇文章读下来,我甚至试图在心里勾勒出了一副作者的肖像。她踽踽独行,在地下室、研究院课程、不快乐的家庭,以及遗失的朋友间游荡。她爱看太宰治的《人间失格》,邱妙津的《鳄鱼手记》\《蒙马特遗书》,她说谁又不曾有过读顾城诗的岁月。 “时间大于死者,已是死亡等身。我还不懂得死亡,已经先明白了时间。” “恨意失去了对象物,终究反向回到了自己。于是太宰说:生而为人,我很抱歉。” 她那些格言式的句子里,试图在告诉我们:敏感是人的本能。她在她的敏感诗意的幻想里、梦境里,重归自由,凌空飞翔。你可以从她的文字里看到这个世界,看到你自己。正像作者言叔夏的导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的,“言叔夏一再地召唤纯真,以抵抗这个正在倾斜下沉的世界,而在不可逆转的死亡与腐败中,却仍要竭力地张开她那一双未被污染的,清亮的眼”。 [台媒专访:天亮前的寂静童梦] 天亮前的寂静童梦——言叔夏《白马走过天亮》 阅读志/提供 好繁华的街一整条灯如流水,好勇敢的灯已经撑起一匹黑夜,好辽阔的夜又淹过来整条的街,每一间餐馆都人声鼎沸。我往下行走,譬如夜游,宛如沿途卖梦。──言叔夏《尺八痴人》 言叔夏钟情于黑夜,不时以文字做出暧昧又亲密的熨贴。她的首本散文集《白马走过天亮》,似乎也特别适合在夜半阅读,总教人舍不得睡,转而捻亮床头灯,窸窸窣窣翻页,追逐她揉塑的一个又一个灰色梦团,然后双手紧握,碎散出满室流云溢彩。 人声杂沓的咖啡馆,言叔夏一人蜷缩在角落座位,逗弄店内的猫,安安静静与世隔绝。待我们上前招呼,她又不若文中冷调疏离,反而腼腆地扬起嘴角。“以前在花莲念书,晚上整个学校都没路灯,我常常一个人骑脚踏车穿梭于夜色里,享受那种被黑暗吞没的感觉。”谈起生活与写作,言叔夏笑说黑夜让人放松,一个人和自己对话也挺不错。至于陪伴,“我想有猫就够了!”她害羞又顽皮地表示。 一个人,晃荡于文字之间 成长于阳光丰沛的南**,言叔夏大学以花莲壤土滋养文学根苗,后又来到溽湿的台北豢养寂寞。她淡薄的身影迁徙过一座座城市,十多年物事流离,在她笔下显得破碎而晦暗,像铺上一层轻愁,雾蒙蒙地似真似幻。 “这可能跟长久以来的生活型态有关,我很难在白天做事,夜晚对我来说相对完整平静,感觉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。”昼伏夜出像只怕生的猫,来去皆孤身一人,有时在夜间出门觅食,每天交谈仅限和店员间的寥寥数语。“其实我不是真的讨厌与人互动,而是会自动呈现放空状态。”她露出一抹不好意思的神情,又接着说无论习惯孤独或投入写作,皆开始于荒谬的中学时代。 “那是一所奇怪的教会贵族学校。”言叔夏神思飘荡至许久许久之前,同学间充满心眼和物质较量,而开学一个月,她几乎没和人说过话:“我好像找不到适合的语言,和他们交流在同一个频率上。而在寻找话语的过程中,也开始尝试写一些东西,可能是幻想出来的人物,藉由他和我一次又一次对话。”百无聊赖的青春期,言叔夏藉由书写虚构另一个自己,被她带着编织未来、逃向远方,甚至经历从未经历过的一切。 想起那段的日子,她日后也写下:“我觉得自己变成这个学校的鬼魂,在魍魉之间晃荡。”即便上了大学仍一如既往,需要与人沟通便依赖网络,她开始习惯在bbs创作或写信。“于是一些故事和风景渐次化作文字,酿成你们所感受到的疏离感。”其实放下社交所需的话术,反倒能听见环境与内心的共振,一如花莲谷地夜车轰隆轰隆擦过睡梦与长夜,竟带来前所未有的宁谧,子宫胎膜般将她牢牢裹住,并且静静守护。 痛的辩证,遗憾的报偿 言叔夏就像时间与空间的拾荒者,发酸的牙、脱壳的衣蛾,种种零碎片段靠她一路捡拾,也能串成透亮的珠炼。又或宅沉的日子也能有超现实转化,时而马戏团在梦中流浪,一下又是鱼怪爬至枕边,湿淋淋地上岸……散文中绵亘诗的质地,又穿插童话般的画面剪辑,都成为她笔下的鲜明特色。 “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声音,当它变成创作时,重要的是这声音被表现的形式,不论散文、小说或是诗,只要能把它说好,便能自成姿态。”因此集结二十七篇文章的《白马走过天亮》,除了爬满迷人诗想,也为作者的生命一再辩证:关于失去、遗憾和死亡。 言叔夏在《辩术之城》如此道出灵魂和身体的疼痛:“痛楚那样真实地来过,每一步每一步都扎扎实实踩在我们的伤口。”自幼父母争吵、伯父精神异常、妹妹怀孕失婚,以及一次次的情感背叛,每回失去都是一场葬礼,在吊唁中扬起生命的尘灰,“所以我能做的,就是将它们扫在同一个格子里,再耐心地好好安置。” 她认真地说,小时候只要犯了错,一定会在心里重新模拟当时的情境好几遍,将自己和这件事调整到一个对的位置。“可能写作就是这样一场仪式吧,它能代替我去整理当下年龄所无法掌控的问题。”言叔夏处理生命经验带有精准控制力,文字不易被情绪左右,尽管往痛处上踩,仍保有一定的抽离,局外人般地看待那些过去。 她说,以前总觉得作品还有很多缺角,好像在雾里看不见自己,但这几年不论生活和认知都来到一个转折,终于拨云见日,开始能平和地组织从前的碎片。 “在这之前就像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。”就像书中记叙,小时候伤心的母亲带她走向海潮,她仍忘不了妈妈身上红艳艳,在风中翻飞的裙襬;却在多年以后,她才发现那是第一次离死亡如此近……言叔夏的文字,总是一再逼视现实本质,却又不时深情回望,让人在若即若离中,看清生命皆是如斯残酷与温柔的反复。 [台媒专访:哀愁的薄翳] 哀愁的薄翳——言叔夏谈《白马走过天亮》 自由时报/提供 和言叔夏多年旧识了。我们是唯二从政大中文所毕业,直攻政大台文博士班的同门师姊弟。同一位指导教授、演练同一套学术规训、同样喜欢日本文学和影剧、同样低调地信守着乏人问津的本质主义。我们很少聊学术,比较常交谈琐碎的近况,对学界及人生的彷徨……她骨感,发长,穿高跟走路叩叩响,思绪敏捷、话速迅雷;她昼伏夜出,极恋房间,声音低沉,豢猫,雅炊,小酌,耽迷星象命理;在人前从不流露过多情绪,深具摩羯座的沉稳内敛,然而上升星座在巨蟹,一扫寡情表象,混熟后是个多情开朗之人。 写散文但行径太像诗人,言叔夏的文学皮肤贴满了隐喻。比方说密闭空间,又尤其是水族箱。幽冥的人造光,帮浦嘟嘟换气,鱼肥草熟,平静无涛便假装是死去活来的海洋。我以为那样的想象是为了躲避现实。现实中的她低调独行,洁身自爱,从认识她以来,就觉得她的内在之核,必然是不甘坚硬而涩楚的。《白马走过天亮》里说,有段时间“日日都在日常中服丧”──这样的基调,注定了她的创作声腔纠缠着起手无回的失落。白驹过隙,日暮无限好,只是途穷。于是乎,她散文里的那些咏叹调,总带有哀愁的薄翳,而那是对现实设下的结界,宣告着明哲保身乃至势不两立。 以柔克刚的禁忌与图腾 言叔夏的创作滥觞自东岸的花莲。与世无争的小镇,山海相亲,边陲大学的同侪对文学艺术怀抱热忱,在在促使她趋策幻想──原生家庭的残缺,剥夺了安全感,虚构的文字顿成自我保护的机制,“像一口箱子那样,可以自然而然将我包裹起来。”家道不幸的撞击,让她太早太早承受了不可告人的痛感。她一度害怕现实的语言,那种指涉性太过明确的东西,往往遮掩着无形的暴力。她迫切需索另一种跳脱日常的、诗意的、迂回的语言,像春蚕吐丝,层层包裹与世隔绝。 如此也就不难想见,何以成年之后的她,习惯离群索居,并且几近病态地迷恋着房间。她是心甘情愿作茧自缚的宅女,宅到无可救药无路可退。箱子、水族箱、房间,加上她喜欢黑色,喜欢夜,以上对她而言,无一不是文学隐喻转嫁至现实日常的防护体系。她的散文濒临以暴治暴,但那暴又不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那种,她无疑有些软弱、透明的质地。是老子说的,以柔克刚。她常令我想起黄碧云的痴与痛。 于是乎,言叔夏总隔着一层距离,周旋在失衡的人际、爱情、亲情。所有伤疤一旦丑过去了,就只剩图腾,透过书写修正它、治愈它,任时间侵蚀,久而久之创伤也就融成身体的形状。言叔夏说她是个对本质主义有所憧憬之人,这样的理念让她的散文带有“一步匮缺无尽期,遍地繁华皆沦丧”的凄怆。她俨然童女睁大双眼,斜睨人寰之败德之狼狈,欲洁不得洁。当所有不幸不堪串连在一块,彷佛是场巨大的丧礼,而她身兼幸存和受灾的角色。 步步为营的哀悼,是《白马走过天亮》最密集的意象。大量超现实的场景切换,类小说的人物设计,穿插日剧式的对白,如梦之梦,如诗之诗,环环相扣。个中人,怨怀无托,嗟情人断绝,究竟谁才是那双妙手,能解连环? 创伤预示:河濑直美及寺山修司 《白马走过天亮》最初向往的书名叫“丧礼森林”──河濑直美的同名电影。言叔夏的创作,自承深受河濑直美与寺山修司的影响。前者擅用干净的镜头,捕捉生命不可或缺的死亡及暴力,毫不造作的坦率、澄澈令言叔夏着迷;后者时常在文学或电影中夹缠着与母亲之间的复杂纠葛。言叔夏说,“寺山的《死者田园祭》里的恐山、小村、捉迷藏、死去的父亲、突然到访的马戏团,有段时间令我完全着迷。”那些霓虹色的电影画片,像滤镜一样地渗透出物象的形貌,同时显影着那看似相悖的死亡、暴力与诗,将隐喻与创伤之间的关系重新洗牌,“某部分可能也影响着我在写作中与母亲的关系。” 历来女作家与母亲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。女性对母体、家庭的幽微观察几乎直见性命。向田邦子、张爱玲、郝誉翔……言叔夏除了大篇幅刻画情伤,连带也逆溯了一切情感破败的肇因:家庭。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里流转,失格的父亲、略带神经质的母亲、未婚怀胎的妹妹、周折来去的恋人……刀刃在不同的掌心你来我往,谁真心谁负心,“每个人都曾是凶手,也都曾被伤害。”言叔夏早熟地预示了一场创伤的范例。自此,她便带着悲剧性的眼神、诗意的保护色泽,俯看周围的人事沦亡衰谢,似乎那样就置身事外,可以让渡成另一枚他者。可以漫不经心隔岸观火,商女不知亡国恨。 再者,除了河濑与寺山的影响之外,夏宇诗中灵动跳跃的节奏感,以及三岛由纪夫对“纯粹性”的念兹在兹,也影响着言叔夏。明知道水中捞月将无所获,三岛怎么也勘不破千尘万色:压抑、绝美、隐忍、无时间性、闭锁的理想本质主义。将欲歙之,必固张之。三岛切割了绝美的纯粹与污浊的现实,于内,四季如春无伤,于外,则是伤烟楚歌……那个曾经害怕自己活不过三十岁的女孩,见证了倩女王祖贤邂逅书生张国荣、也融入流行歌大行其道的90年代,眼睁睁看着一票作家前仆后继自残凋零。那样死伤惨重的背景,恰恰是言叔夏青春正盛的时期,于是内在本质挥之不去某种早夭的、哀愁的预感:长路漫漫,何处是归途。 言语的指涉:隐身术抑或障眼法? 言叔夏的隐喻习癖就像《百年孤独》那样,每件事物都迫不及待需要归属,每个词语都需要剑及履及的指涉。那就像是一种隐身术或障眼法。她说,“如果每个东西都是一种隐喻,世界会变得很危险。隐喻只能发生在写作的世界里。”这样的隐喻对她而言,就是隐身术或障眼法,举重若轻抚润了现实的粗砺。 她说,“散文的叙述声腔最能表现一个人的质感。”人际关系便藉由这样的质感,相互吸引或排拒。浸淫学界多年,熟稔各种文学理论和文本分析的操演,连带影响她思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时候,仍能井然有序地归纳。“沉重的事物需要被完整倾诉,而学术恰好提供我一条迹线,去找回事物原来的秩序。”尤其在人生最混乱的片刻,她往往嗜读理论,藉此将人与人的关系抽象化,此举情同疗伤止暴。我忽然想起《月亮一宫人》里,母亲对她说:“有人要来靠近你,不要轻易把心交出去……”忧郁的童女仍睁大双眼,凝视着你来我往的真心和负心交战,只是白马走过天亮之后,没有人能保证生命永恒丽如夏花,毕竟有些刀刃总是要先拿来对自己,才能在彻骨之际,赎回心的醒悟。 [精彩试读] 父 亲 年轻时写的小说被朋友P君说:“为何你故事里的人,总有一个诗意(且几近不存在)的父亲?而母亲总是家庭剧场里唯一留下来和女儿对峙的角色?”几年过去后重新回想起这段话,我想到十九、二十岁时的离家时光,开始独居的日子。那确实也是父亲真正从我们的家庭剧场离去的时间,奇怪的是我一点也没有感到过哀伤,甚至有种早该如此的感觉。童年时的父亲是个不擅言辞的男子,拥有甲状腺亢进的宿疾。我还记得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作业,因为解不出习作上的算术问题,父亲一把掀掉我正在做功课的小甜甜矮桌。由于整个过程实在太突兀,以致长大以后在希腊神话的课堂上读到海神波赛顿时,总是没来由地想起了父亲。那当然不是他所愿意的,只是一种腺体的激素分泌而已。童年时代的我如此理解愤怒。于是在长大以后的许多亟需激情的场合,我总是本能性地用一种观看显微镜筒里切割叶片的细胞般的态度,让自己从漩涡的核心隐退下来。童年的我告诉自己:父亲并不能伤害我。 父亲的膝盖里有一块铁片,母亲说那是年轻时因工作受伤所放置的,用来支撑左腿的关节。在我的身高尚不及父亲大腿一半的年纪时,这条伤疤日日都来到我视线的水平范畴,取代了父亲的脸孔。它像是一条神秘的拉链,通往我与父亲之间共有的那面濒临悬崖的海沟。我有时会想象那块铁片,在父亲腿骨的组织间蜉蝣般地漂流。以致后来当我想起父亲的侧脸时,不知为何总必伴随着那条锯齿状的伤口,像是被针所缝补过。父亲在我的小说里,成为高帽子的厨师、离家出走的寄居蟹、单脚的加西加卡吉普赛歌手……小说里的父亲总像从马奎斯的南美洲森林里走出的人物,热烈、诗意,擅长魔术。在那重复性来临的书写之中,我渐渐遗忘了父亲真正的脸孔。 我忘记第一次被父亲高高扛起在肩头,差一点就能触摸到日光灯管的惊恐颤抖。我甚至忘记那时的我是一个多么不安的女儿。自闭,瑟缩,害怕人类。可以耗费整个下午观察水沟盖里不断涌出的蚁群。父亲总是在傍晚回来。我们出发去一个街角的书店。那是九○年代初期乡下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书店,混杂着黄昏水果店与面摊的嘈杂声。街灯刚刚亮起,天还没有全部暗下去,呈现一种透明的蓝色。那种蓝色使四周的一切都阴暗了下去。 父亲从那样的阴暗中抬起头来,隔着背光的书架,他眯着狐狸面具般的脸孔,微笑地俯身对我说:“长大以后,要不要当小说家?”我非常讶异地回视了他。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对我说出这么暴露的话,也不知道父亲是否明白他所说出的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暗示,暗示我们此后必将永远处在佚失与追捕的循环之中。而仿佛为了防止这个预言成真,此后我再也没有给父亲看过我的任何一篇文章;但是,即使是如此,父亲仍在我十八岁的某一天夜里根茎植物般地原地消失。我忽然理解,所谓的语言,就是命运。父亲离家以后,我总想不起最后一次看到他的脸孔,五官的排列组合。我只能想起那个童年时代与我的视线齐高的膝盖伤口,还有那块看不见的铁片,鱼一般地割开了记忆的薄膜。十年以后父亲重新回到家,仿佛出门远行的尤利西斯,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,是不是也在航行的路上受过赛伦海妖的引诱。十年里我与母亲、妹妹和弟弟,像是一支失去了领队而终于各自溃散到沿途城市的骆驼商旅。父亲终于成为我童年时代的幻想,成为一个小说里的人。我使用这个“爸爸”长达十年之久,像一具疲软松弛的体腔。而十年后回家的父亲进门穿上了这件松软的皮囊,安静地坐在一旁进食了起来。我知道父亲其实哪里也没有去,他一直端坐在晚餐的餐桌,从来也不是尤利西斯;我忽然明白,从那个黄昏的书店开始,尤利西斯就已经是我。是我离开了这张桌子,去寻找那砂画般佚散的父亲的脸孔。 秃头女高音 我总是在公交车上遇见那些女人。那些初老的女人。那些初老的女人爬上车来时,公交车的日光灯管啪嚓啪嚓地闪了闪。是夜间七点钟那种除了吃饭不知该做什么好的时间。车厢空荡荡的。你想:这是一个女人。这是一个老上班女人。她们的前额都秃了。 我从没见过女人那么秃。发旋那么大。像一个嘴巴。可她们看起来都并不是很想的样子。你想不出她们会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,想逛的小店,想买的衣服。正确地说,她们不是极饥饿就是极洁癖。你总想:一个老上班女子。好像从年轻起就很熟练国税局的报账作业或法律规则。戴藏青色袖套。躲在一方屏幕背里这边打打,那边敲敲。指纹磨得很平很平。穿假皮包鞋。终年背同一只灰咖啡色GUCCI手袋。她们老搽同一色的口红让你以为她们其实私下有某种串供,类似都去上了初老学校礼仪课程。你总想:这是一个初老女子。她没老到需要被你起身让座。你想:这样一个初老女子。女子老了以后都纷纷变成了男子。你老是想:这样一个像男子的初老女子。她这么老了还要工作。她好像从来没用过她的子宫。 我也会有那样的初老时光吗?我从年轻起就独自居住在不同城市的各种房子里。在河边的公寓时我曾想过也许一生都要住在这个房间里,晨起目视着落地窗外流淌的河直至老去。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。我在那里面度过非常安静的几年。结束了硕士论文,并且开始博士论文。房东是一个中年女子,从不曾来过。我曾想过我会在这个房间里慢慢变老,老到我终于要离开这座房子的时候我会再见到她。那时她变得更老而我已经是一个初老女子,仿佛这中间的几十年全都不存在。我梦想着这样的见面到来。后来我终究离开了那座房子,因为房东先于我的初老把它卖了。“我要到塞尔维亚去了。”最后一次见面时她说。“塞尔维亚是什么地方?”我忽然发现她已是一个初老女子。 到五十岁的时候,我还会在这个城市生活吗?成为那些夜间七点钟大量出现的初老女子们。发线退得太高于是就索性成为了光头。一直独居。偶尔和不结婚的同志友人见面吃饭。抱怨皱纹和体脂肪。谁谁谁听说艾滋死了你知道吗。老到一定程度AIDS就跟Cancer没两样。喷嚏感冒似的老Gay与老女。然后也在工作。又老不到可以退休的年纪。仍每天都在学习新的计算机系统。 据说女子的耳朵愈老愈听不见低音,于是她们不再听见男子的话语。她们的声带随着这种构造拔得极高,终于将只能听见自己与海豚的声响。夜间七点钟的公交车上,我忽然就理解了整个车厢,为何如此静默。如此针一般地静默。 |
1、如非特殊说明,本站对提供的源码不拥有任何权利,其版权归原著者拥有。
2、本网站所有源码和软件均为作者提供和网友推荐收集整理而来,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。
3、如有侵犯你版权的,请来信(邮箱:123456@qq.com)指出,核实后,本站将立即改正。